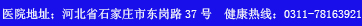慢性丙型肝炎患者干扰素诱发甲状腺炎的研究
2017-9-14 来源:不详 浏览次数:次本文原载于《国际流行病学传染病学杂志》年第5期
HCV感染不仅是慢性丙型肝炎(CHC)的常见原因,还易致肝外病变,尤其是应用IFN治疗者,常引起甲状腺功能异常[1]。随着CHC新型治疗药物应用于临床,大部分患者可以实现治愈,但我国现阶段CHC患者抗病毒治疗的标准方案仍是IFN联合利巴韦林(RBV)。应用IFN治疗的不良反应有流感样症状、骨髓抑制、甲状腺疾病等,其中IFN诱发的甲状腺炎(IIT)是常见的内分泌系统不良反应[2]。据报道,IIT发生率为3.9%~27.2%。部分患者由于IIT而中断治疗[3]。本文就HCV感染及IFN治疗诱发的甲状腺疾病的关系、IIT的分型、应对策略及转归等方面的研究作一综述。
一、HCV感染及IFN治疗与甲状腺疾病的关系一项Meta研究结果显示,CHC患者在IFN治疗前甲状腺疾病发生率为4.6%~21.3%,治疗期间为1.1%~21.3%,治疗结束后为6.7%~21.3%[4]。而普通人群甲状腺疾病的发生率为3.5%~4.0%[5]。究竟是HCV本身增加甲状腺疾病的发生,还是IFN增加了这种概率目前还不明确。多数研究表明,HCV和IFN可能对IIT的发生发挥了协同作用[6]。
1.HCV感染与甲状腺疾病的关系
目前普遍认同的HCV相关甲状腺疾病的发生机制主要为旁道激活和分子模拟理论。前者指HCV感染甲状腺细胞导致局部炎症反应,释放IL-8等细胞因子,从而激活原本受Treg等免疫调节细胞抑制的原位T淋巴细胞,诱发自身免疫造成甲状腺组织损伤和激素分泌异常[7]。当HCV感染后,甲状腺细胞可产生内源性的IFN-α和IFN-β,激活NK细胞、记忆性T细胞、DC等,产生甲状腺自身抗体(TAb),导致IIT发生;后者认为HCV蛋白与患者自身蛋白有部分相近的氨基酸序列,引起机体对自身抗原产生交叉免疫应答,产生多种自身抗体,造成甲状腺及其它组织的损伤[8]。有文献表明CHC患者自身抗体发生率为32%~46%[9]。还有文献显示无论是否应用IFN,CHC患者TAb水平均升高2%~48%[10]。这些研究都支持HCV与人类自身抗原间存在分子模拟的假设。另外,Akeno等[11]认为即使HCV不感染甲状腺组织,HCVE2蛋白也可直接作用于甲状腺细胞,与CD81分子结合上调IL-8表达,激活T细胞并诱导细胞凋亡。
2.IFN治疗诱发甲状腺疾病的作用机制
据观察,约40%的CHC患者在IFN治疗后发生了IIT[12]。目前公认的IIT发病机制是IFN对免疫系统的调节作用和对甲状腺细胞的直接作用。IFN可通过激活双向激酶信号传导及转录催化通路(JAK-STAT),导致大量的IFN刺激基因(ISGs)转录,包括细胞因子和黏附分子基因转录,这些可诱发甲状腺自身免疫,增加甲状腺上皮细胞MCH1的表达,这种过表达,可以导致甲状腺组织损伤和炎症反应[12,13];IFN与细胞膜上特异性受体结合后形成新的抗病毒蛋白,增强NK细胞、DC和淋巴细胞的活性,抑制T细胞凋亡,激活中性粒细胞和单核细胞,并刺激IL-6、B46、Cw7等细胞因子的释放,IL-6等与甲状腺上皮细胞特异性结合后可降低促甲状腺激素(TSH)调节的摄碘率和甲状腺激素的释放[13]。据报道CHC患者发展成IIT是发生了Th1免疫应答的分化[14],而IFN治疗可改变Th1调节的免疫应答,并促进TGF-β、IL-10表达加重炎症应答[15]。
IFN治疗期间发生IIT的患者中还有50%不产生TAb,提示IFN对甲状腺也有直接毒性作用,包括抑制甲状腺激素的合成、分泌和代谢。Caraccio等[16]发现IFN在甲状腺滤泡细胞聚集时,可抑制TSH诱导基因,如甲状腺球蛋白(TG)、甲状腺过氧化物酶(TPO)及碘钠同向转运子的基因表达,从而抑制碘摄取和甲状腺激素的分泌。另有研究表明IFN能模拟甲状腺刺激因子直接抑制甲状腺激素合成和释放[17]。还有学者发现,将甲状腺细胞暴露于IFN环境中,TSH受体基因表达被上调,从而导致甲状腺滤泡细胞死亡[12]。
二、IFN治疗与不同类型IIT的关系CHC患者常见的IIT从病因上分为自身免疫性和非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。前者分为Graves病(GD)、桥本甲状腺炎(HT)和无症状的TAb阳性;后者分为破坏性甲状腺炎和非自身免疫性甲状腺功能减退[18]。
1.GD
GD多有明显的甲状腺功能亢进(甲亢)症状且TSH降低、甲状腺激素水平升高,伴有TAb阳性和(或)甲状腺扫描显示吸碘率增加。GD在IIT中较少见[19]。多数报道显示,GD在CHC患者终止IFN治疗后仍不能完全缓解,提示IFN可能诱导一些有GD倾向的患者发病[19,20,21]。
2.HT
大多数的IIT患者表现为HT[19]。特点是出现TAb和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(甲减),伴或不伴有甲状腺肿大。Watanabe等[22]报道3例CHC患者在IFN治疗后出现甲减并需甲状腺素替代治疗,这3例患者在治疗前均检出TAb,且治疗后TAb水平明显升高,提示IFN诱导了易感患者HT进展。多数文献表明通过甲状腺素替代治疗,HT患者能够完成IFN疗程[23]。
3.无症状的TAb阳性
研究显示,未接受IFN治疗的CHC患者TAb阳性率约为5%~10%,TAb的产生常是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的临床前期,IFN治疗前TAb阳性的个体在治疗中TAb水平可能增加[24]。IFN治疗结束后部分患者仍可能出现TAb,这部分患者很有可能会进展为临床甲状腺疾病[25]。
4.破坏性甲状腺炎
此类患者通常TSH受体抗体(TRAb)阴性、摄碘率降低[18],常表现为突发的甲亢,可伴有发热及颈痛,继而为甲减期,最终在数周至数月内甲状腺功能恢复正常,不足5%的患者会进展至永久性甲减[26]。IFN治疗发生甲亢患者超过50%被诊断为破坏性甲状腺炎,其余为GD。多数破坏性甲状腺炎患者临床症状不明显,或被IFN的不良反应掩盖,且停止IFN治疗后多能自行恢复,因此它的实际发生率可能更高[12]。
5.非自身免疫性甲状腺功能减退
部分临床或亚临床甲减患者,检测TAb为阴性。这些患者的甲减常是一过性的,治疗期间或治疗结束后即恢复正常[12]。但患者产生TAb后发展为永久性甲状腺炎的概率会增加[25]。
三、IIT患者的应对策略多数文献报道凡是药物可以控制的甲状腺疾病,IFN不必减量或停用[9,23]。而由于甲状腺疾病的许多表现可能与HCV感染症状及IFN、RBV联合治疗中的不良反应重叠,临床医师更应重视甲状腺功能的筛查。所有患者治疗前都应检测TSH和TAb,如果指标正常,应在治疗中和治疗结束后每隔3个月复查一次TSH。IIT可发生于IFN治疗的任何阶段,早在治疗后第4周,晚在治疗结束后12个月[27]。因此应进行3个月一次的TSH水平检测以避免诊断和治疗的延误。如果检测TSH正常,TAb阳性,那么此类患者发生IIT的风险高,建议每1个月检测一次TSH水平以及时发现IIT[4]。如果检测TSH异常,则需要下述检查及相应的处理。
(1)TSH降低:应进一步检测甲状腺激素及TAb水平。如果检查结果与破坏性甲状腺炎一致,有症状患者可用β受体阻滞剂治疗,同时需密切监测甲减(常在甲亢后的数周至数月内出现)的发生。多数病例治疗是有效的,能继续IFN治疗,但要注意继续使用IFN可能引起破坏性甲状腺炎的复发和更严重的甲亢。如果检查结果提示为GD,对于肝功能恢复正常的患者可使用抗甲状腺药物治疗,定期检测肝功能及血常规;对于肝功能仍异常者,抗甲状腺药物的使用可能会加重肝损害,或抗甲状腺药物治疗无效时可考虑放射性碘和(或)手术治疗[28]。
(2)TSH升高:同样需检测甲状腺激素及TAb水平。大部分患者通过甲状腺素替代治疗无需终止IFN使用。由于甲减的进展会导致替代需求增加,建议每隔1~2个月复查TSH以及时调整替代治疗剂量,IFN治疗结束时替代需求可能会减少甚至降至没有[12]。治疗结束后伴有高滴度TAb的HT患者多需要长期治疗[25]。
四、IIT患者的转归及病毒学应答关于IIT远期预后的临床研究结果不太一致。一些报道显示所有患者均能恢复[9,29],其中一项前瞻性研究纳入例CHC患者,治疗结束后共18例患者发生IIT,所有患者在3年的随访研究结束时TSH及TAb均恢复正常[29]。而另一些研究显示仅部分患者可恢复[19,20,21],Czarnywojtek等[19]对例CHC患者分析,其中26例GD患者在放射性碘治疗后仅有17例恢复,6例进展为持续性甲减,3例仍为甲亢;另一项研究报道,4例GD患者和10例HT患者中分别有3例和8例在IFN治疗结束后TSH不能恢复,4例破坏性甲状腺炎患者TSH均正常,提示非免疫因素较免疫因素导致的IIT容易恢复,IIT是否恢复与是否终止IFN治疗无关[20]。
此外,有报道称IIT是获得较高SVR的预测因素[2,9,21]。Hwang等[21]对例IFN治疗的CHC患者分析,67例IIT患者与例非IIT患者的SVR率分别为65.7%和49.1%,提示IIT患者获得更高SVR率。但多数研究认为IIT与SVR并不相关[24,28,29,30]。
五、小结综上所述,IIT的发病机制目前尚不完全清楚;对IIT的治疗、转归及与病毒学应答还没有统一结论。现有的治疗策略多为经验总结,有待于更长期的大样本研究。鉴于IIT的发生率高,对确实需要接受IFN治疗的CHC患者,强调在治疗前、治疗过程中、治疗结束后常规监测TSH和TAb,以期实现早诊断、早治疗,减少其发生和发展。
参考文献(略)
赞赏